茶马商都的记忆
这里是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上的要塞,这里是明清时期西北地区最大的“茶马互市”。日月山下的古城丹噶尔就这样从历史中走来。
曾经的古道已经变成现代的公路。从青海省省会西宁出发,沿109国道向西行驶约50公里,便可以到达青海省湟源县的丹噶尔古城。作为海藏咽喉,这里依然是青藏公路线上由内地通往西部牧区前往西藏的重要通道,也是青藏高原农业区进入牧业区的分界地区。
丹噶尔,是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意思是“白海螺”。丹噶尔古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距今有已600多年历史。自西汉以来,这里便是各民族进行商业贸易的中心。随着贸易的繁荣与发展,唐王朝与吐蕃在湟源境内日月山下设立了青藏高原上第一个“茶马互市”。到了清中晚期,“茶马互市”逐渐移到丹噶尔古城,并逐渐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之一。因此,丹噶尔古城素来享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小北京”等众多美誉。
走在丹噶尔古城青石铺路的街巷里,闪亮的排灯照射着街道旁古香古色的各色商号,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商业兴隆的藏汉茶马互市时代。
丹噶尔作为一座西陲古城,它在历史上又与汉、藏、蒙、回多民族经济贸易的这种需求,逐渐形成的一个文化集散地。它的价值在于,它通过这种贸易以及边陲古城的形态,促进了多民族经济文化的这种认同、交流,甚至是变异。使得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多民族文化共生共融,而且能够和睦相处,和而不同,这样一个良好的多元文化,使得它具有了代表性和象征性,使得丹噶尔这个西部的古城在多民族地区,特别是在西部多民族地区,具有了它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
解说:现在的丹噶尔古城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完美再现了昔日商业繁荣的景象。路边仿古商号里,依然在经营各类藏族手工艺品和青藏特产。游人依稀可以找寻到古城当初的繁荣。
与丹噶尔古城贸易的繁荣同时诞生的还有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一种职业--藏客。在湟源县,“藏客”这个久远的称谓还留存在很多老人的记忆深处,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曾赶着马帮和牦牛驮队,把丝绸、茶叶等日用品运到高原,换取这里的马匹、皮毛和中藏药材。这些从事汉藏贸易的藏客,曾经来往于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唐蕃古道。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卓绝的抗争,翻越千山万水,年复一年地往来于汉藏两地,通过物资的交换,带动了多民族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大贯通。
1954年青藏公路通车前,进藏,并非易事,从湟源到拉萨,行程6000多华里,历时4个多月,对于藏客们来说,漫长的唐蕃古道注定是一条不平凡的路途,充满了不可预知的危险。现在生活在湟源县日月乡尕庄村的李学军就是这样一位“藏客”后代。
原来我的爷爷就是藏客。他走藏的时候听说是从湟源丹噶尔古城买些从内地过来的比如从四川一带过来的布匹、茶叶、湟源陈醋、青稞之类的用马队驼(到西藏)。驼上去以后,路上也是非常艰难,我爷爷去世前头上还有一个疤,这个疤是当时土匪抢东西是砍伤留下来的。(他们从西藏)回来时他们把西藏从印度的茯茶、味道也特别香,方方正正的用麻绳捆住的,还有从印度拿过来的藏红花、藏茵陈,还有些野兽的皮毛,到湟源以后在丹噶尔古城做生意。听说一趟来回得半年。
藏客们奋力前行的脚步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藏公路开通的汽车鸣笛声中渐行渐远。岁月悠悠,当年那些体格健壮的藏客如今大多离世,留下的也早已成为耄耋老人。但藏客的传奇经历令他们一生都铭心刻骨,“藏客”的称谓也伴随光阴的流逝化为一个历史符号,镌刻在了丹噶尔的城谱里。
但古城并没有随着藏客历史的远去而停下前进的脚步。处于西宁大旅游圈和青海湖旅游圈的交集处的丹噶尔,如今成为了通向世界第三级青藏高原的平台和青藏旅游线上的必经站。每年农历正月元宵节前后,几百盏排灯同时展出,从古城西门“拱海门”到东门“迎春门”,延伸到“丰盛街”至“火祖阁”,灯火辉煌,璀璨耀目,成为古城一道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风景线。街道两旁店铺中的酒曲、平弦,激扬清脆的旋律,如摇落了满天的星星,或柳叶款款在风中摇曳。这座兴盛了千年的互市古城华丽转身,承接千年来的商业繁荣,延续新的藏汉交流传奇。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33
- 34
- 35
- 36
- 37
- 38
- 39
- 40
- 41
- 42
- 43
- 44
- 45
- 46
- 47
- 48
- 49
- 50
- 51
- 52
- 53
- 54
- 55
- 56
- 57
- 58
- 59
- 60
- 61
- 62
- 63
- 64
- 65
- 66
- 67
- 68
- 69
- 70
- 71
- 72
- 73
- 74
- 75
- 76
- 77
- 78
- 79
- 80
- 81
- 82
- 83
- 84
- 85
- 86
- 87
- 88
- 89
- 90
- 91
- 92
- 93
- 94
- 95
- 96
- 97
- 98
- 99
- 100
- 101
- 102
-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 113
- 114
- 115
- 116
- 117
- 118
- 119
- 120
- 121
- 122
- 123
- 124
- 125
- 126
- 127
- 128
- 129
- 130
- 131
- 132
- 133
- 134
- 135
- 136
- 137
- 138
- 139
- 140
- 141
- 142
- 143
- 144
- 145
- 146
- 147
- 148
- 149
- 150
- 151
- 152
- 153
- 154
- 155
- 156
- 157
- 158
- 159
- 160
- 161
- 162
- 163
- 164
- 165
- 166
- 167
- 168
- 169
- 170
- 171
- 172
- 173
- 174
- 175
- 176
- 177
- 178
- 179
- 180
- 181
- 182
- 183
- 184
- 185
- 186
- 187
- 188
- 189
- 190
- 191
- 192
- 193
- 194
- 195
- 196
- 197
- 198
- 199
- 200
- 201
- 202
- 203
- 204
- 205
- 206
- 207
- 208
- 209
- 210
- 211
- 212
- 213
- 214
- 215
- 216
- 217
- 218
- 219
- 220
- 221
- 222
- 223
- 224
- 225
- 226
- 227
- 228
- 229
- 230
- 231
- 232
- 233
- 234
- 235
- 236
- 237
- 238
- 239
- 240
- 241
- 242
- 243
- 244
- 245
- 246
- 247
- 248
- 249
- 250
- 251
- 252
- 253
- 254
- 255
- 256
- 257
- 258
- 259
- 260
- 261
- 262
- 263
- 264
- 265
- 266
- 267
- 268
- 269
- 270
- 271
- 272
- 273
- 274
- 275
- 276
- 277
- 278
- 279
- 280
- 281
- 282
- 283
- 284
- 285
- 286
- 287
- 288
- 289
- 290
- 291
- 292
- 293
- 294
- 295
- 296
- 297
- 298
- 299
- 300
- 301
- 302
- 303
- 304
- 305
- 306
- 307
- 308
- 309
- 310
- 311
- 312
- 313
- 314
- 315
- 316
- 317
- 318
- 319
- 320
- 321
- 322
- 323
- 324
- 325
- 326
- 327
- 328
- 329
- 330
- 331
- 332
- 333
- 334
- 335
- 336
- 337
- 338
- 339
- 340
- 341
- 342
- 343
- 344
- 345
- 346
- 347
- 348
- 349
- 350
- 351
- 352
- 353
- 354
- 355
- 356
- 357
- 358
- 359
- 360
- 361
- 362
- 363
- 364
- 365
- 366
- 367
- 368
- 369
- 370
- 371
- 372
- 373
- 374
- 375
- 376
- 377
- 378
- 379
- 380
- 381
- 382
- 383
- 384
- 385
- 386
- 387
- 388
- 389
- 390
- 391
- 392
- 393
- 394
- 395
- 396
- 397
- 398
- 399
- 400
- 401
- 402
- 403
- 404
- 405
- 406
- 407
- 408
- 409
- 410
- 411
- 412
- 413
- 414
- 415
- 416
- 417
- 418
- 419
- 420
- 421
- 422
- 423
- 424
- 425
- 426
- 427
- 428
- 429
- 430
- 431
- 432
- 433
- 434
- 435
- 436
- 437
- 438
- 439
- 440
- 441
- 442
- 443
- 444
- 445
- 446
- 447
- 448
- 449
- 450
- 451
- 452
- 453
- 454
- 455
- 456
- 457
- 458
- 459
- 460
- 461
- 462
- 463
- 464
- 465
- 466
- 467
- 468
- 469
- 470
- 471
- 472
- 473
- 474
- 475
- 476
- 477
- 478
- 479
- 480
- 481
- 482
- 483
- 484
- 485
- 486
- 487
- 488
- 489
- 490
- 491
- 492
- 493
- 494
- 495
- 496
- 497
- 498
- 499
- 500
- 501
- 502
- 503
- 504
- 505
- 506
- 507
- 508
- 509
- 510
- 511
- 512
- 513
- 514
- 515
- 516
- 517
- 518
- 519
- 520
- 521
- 522
- 523
- 524
- 525
- 526
- 527
- 528
- 529
- 530
- 531
- 532
- 533
- 534
- 535
- 536
- 537
- 538
- 539
- 540
- 541
- 542
- 543
- 544
- 545
- 546
- 547
- 548
- 549
- 550
- 551
- 552
- 553
- 554
- 555
- 556
- 557
- 558
- 559
- 560
- 561
- 562
- 563
- 564
- 565
- 566
- 567
- 568
- 569
- 570
- 571
- 572
- 573
- 574
- 575
- 576
- 577
- 578
- 579
- 580
- 581
- 582
- 583
- 584
- 585
- 586
- 587
- 588
- 589
- 590
- 591
- 592
- 593
- 594
- 595
- 596
- 597
- 598
- 599
- 600
- 601
- 602
- 603
- 604
- 605
- 606
- 607
- 608
- 609
- 610
- 611
- 612
- 613
- 614
- 615
- 616
- 617
- 618
- 619
- 620
- 621
- 622
- 623
- 624
- 625
- 626
- 627
- 628
- 629
- 630
- 631
- 632
- 633
- 634
- 635
- 636
- 637
- 638
- 639
- 640
- 641
- 642
- 643
- 644
- 645
- 646
- 647
- 648
- 649
- 650
- 651
- 652
- 653
- 654
- 655
- 656
- 657
- 658
- 659
- 660
- 661
- 662
- 663
- 664
- 665
- 666
- 667
- 668
- 669
- 670
- 671
- 672
- 673
- 674
- 675
- 676
- 677
- 678
- 679
- 680
- 681
- 682
- 683
- 684
- 685
- 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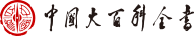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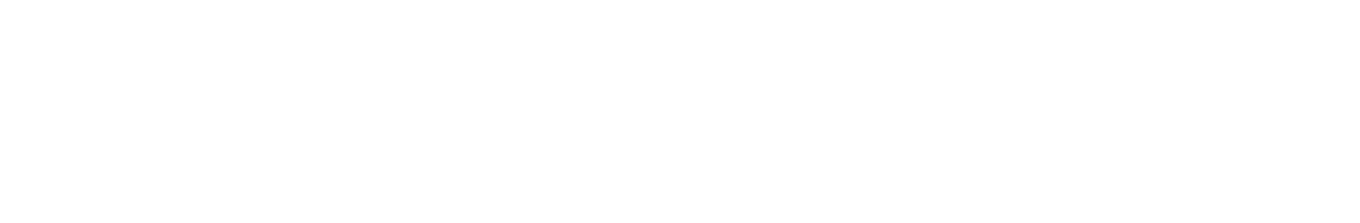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