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士大夫及士风和名节(二)
在当今中国大陆史学界的精英论大扩张、大泛滥之际,中国大陆的民众却没有按史学界精英论的说教,顶礼膜拜于精英们的足下。说来也简单,其实无非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之间的剥削和压迫正是产生所谓“仇富心理”的基本原因。愚以为,精英论之说无非是服务于剥削和统治阶级,为之美化;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却是服务于广大的被剥削和被统治阶级,为之谋解放,这大致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和分歧。仅就所谓“仇富心理”而言,也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比所谓精英论更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检验。
在今存史料中,似乎真正称得上精英的所占比例较大,这根本不能说明实际情况。
第一,因为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一般都是士大夫的手笔。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实际上某种意义上就是成天与古代士大夫打交道,实行单向交流。他交流给我们,我们没法交流给他们。时间久了,就会产生错觉,不做具体分析,实际上就笼统地将士大夫视为群体性,至少是主干性的社会中坚和时代精英,是多少遏制皇帝胡作非为的开明势力,似乎士大夫群体至少是程度不等或表现各异地担当着中华古政治史演进的正面甚至主导角色,这不符合史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史观。
我在学生时代就学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从来没有看重士大夫。学生发问了,我才重新考虑这些问题。按我的想法,士大夫就是士大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结果学生一提到士大夫,就觉得很了不起,才引起我的思考。
我在总体上鄙视士大夫群体,也看重个别真正精英人物,他们确实是“中国的脊梁”。宋代士大夫有几个杰出代表,如范仲淹、李纲、宗泽、文天祥、陆秀夫等,确实是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精英。
我有一次翻《襄毅文集》,看到有一段话说:“自古天生拨乱反正之大材,多见抑于颠危,见忌于群小,使之因挫辱排挤,以长养其刚大不可屈之正气。”宋代有些士大夫确实是“刚大不可屈之正气”,能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出来。所谓“群小”,就是些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这就是阶级社会的客观情况。
马克思主义批判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大染缸。古往今来的大量史实证明,在阶级社会中,指望统治和剥削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能够成为恪守道德、循规蹈矩者不过是天真而荒唐的幻想。
鲁西奇教授说“从前没有一个好人”,我倒觉得还是有好人的,不能说完全没有。李纲、宗泽还是好的。他认为没有一个好人,比我看得更决绝。
再讲古代的士风和名节、气节问题。
“士风”最初只是一个褒义词。大概到了宋代,“士风”转变成为一个中性名词。比如“举人作讼,以觊覆考”,举人要告状,希望重新考试,就“颇亏士风”。《朱子语类》说“今日士风如此,何时是太平?”多是把士风当作中性名词。
顾炎武《生员论》说“以十分之七计,而保身家之生员殆有三十五万人,此与设科之初意悖,而非国家之益也。”“今之生员以关节得者,十且七、八矣”。这个生员大多数是冒牌的、买来的,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不是凭自己的文化水平拿来的。
按照士大夫的标准,生员确实是士大夫。但《生员论》对明清社会的士大夫做了定量分析。他说生员一个是来路不正,很多人是假冒的,一个是成了地方上恶势力,官府拿他没办法。这就是明清士大夫的实际情况。明清有一个晋升阶级,同科举是连在一起的。生员比举人还低,因为举人要中举,生员不用中举,有国子监监生或者什么生都算生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生员至少大多数就是当地的地主,而依前引宋人陈亮的标准,就算是乡士大夫。其士风的主流如何,就不需要对顾炎武的说法再加引申了。
中国古代历代最强调名节和气节是东汉和宋。东汉诗人经常说,“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但是尽管如此,东汉诗人崇尚名节并不是铁板一块。
比如历史记载,汉灵帝的时候,宦官“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古代的“党”字,一般都是贬义词。“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这些士大夫都是不敢说话的样子。
当时有一个叫崔烈的,东汉大族,几代为公。崔氏,后来成了大族清河崔氏。当时汉灵帝要卖官,崔烈出钱买到了三公。他问儿子崔钧,“我现在居三公了,大家怎么议论?”崔钧说:“你这个大人,年纪少的时候,有好的名誉,不认为你不应当三公,但是现在到了三公地位,天下失望了。”崔烈说:“为什么?”他说:“大家嫌弃铜臭。”结果崔烈大怒,举杖打儿子。
我写过一篇文章,叫《绍兴和议与士人气节》。这篇文章讲述了在秦桧和宋高宗威逼利诱之下,成千上万的士人附会绍兴和议。南宋刘宰感慨当时的士风和文风,他评论说“文以气为主,年来士大夫苟于荣进”,就是要往上面钻营。“冒干货赂”,就是要贪污行贿,所以写出来的文章都是“奄奄无生气”。
一般来说,宋朝强调士风是从范文正公——范仲淹开始的。范仲淹有两条著名的言论,一条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一条是“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唐宋时候,罪分公罪、私罪两种。贪污是私罪。冒犯上司,比如范仲淹,劝宋仁宗不废皇后,后来被贬逐,到地方上做官,就是公罪。他认为,要做官,公罪也没法避免。因为在肮脏官场里,要主持正义,必须得罪人、得罪上司,公罪就逃不了。但私罪不能有。所以叫“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句话最早不是我引用的,是美籍爱国华人学者刘子健先生先引用的。
范仲淹是公认的在倡导名节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的人。另一个是欧阳修。欧阳修强调气节,特别批判了五代纷争之际的冯道。冯道是作为正面形象的,但他对冯道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说“天下大乱,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道(方)自号‘长乐老’,著书数百言,陈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阶勋官爵以为荣”,说他自己换了四个皇帝,四个朝,得到官爵以为荣。“事九君”,侍奉九个皇帝,“未尝谏诤”。于是,“长乐老”就输了理。至少宋朝,没有一个人从此以后再公开提出来,为“长乐老”辩护。这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到了21世纪,还人提出来为秦桧之流辩护。
是不是因为范仲淹、欧阳修的提倡,宋人的士风变好了呢?不是这样的。
当时,宋朝以儒立国,强调儒学。辽朝不是这样,但辽朝亡国的时候,死难的死义之臣,至少并不比宋少,甚至还比宋多一点。当时金人围攻开封,开封围城里,只有李若水一个人。辽朝亡国有多少人,这些人现在没有记载留下来。
北宋末,爆发了著名的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当时大概有几百个太学生随他一起上书,有一些太学生在开封城破以后,也表现了爱国气节。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太学生里照样有卑鄙无耻之徒。金人攻破开封城以后,“索太学生”,愿意为金朝服务。招募80个人,报名的居然有100个人。到了军前,金人威胁他们,说不要他们做大义策论,只要他们谈乡土情况、方略利害。这些人纷纷拿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献给金人。还有的没有老婆,原来有一些妓女勾搭,就把这些妓女当作自己的妻子,弄到金军里。金人感觉到这些人不行,退了60多个人。当时金朝习惯同清朝一样,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头发剃光了也梳上辫子。从现在考古发掘看,女真人都是两条辫子。剃了头发,金人退兵以后,有些人裸体逃回来,丑态百出。
统计算了一下,宋朝太学生的数量在宋神宗元丰时是2400人,宋徽宗崇宁时增加到3800人,后来人数有所减少。但伏阙上书的人、无耻降金的人,多是少数,多数人因为有各种原因没有参加,在危难时刻没有挺身而出。
再就南宋末年的死难者做一统计。这个统计表不全。《宋史》《文天祥传》《忠义传》《昭忠录》,以及《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六《诗》、卷十九《文丞相督府忠义传》等所记录南宋末殉难人物颇多。根据我查的结果,士大夫有86人,武官有42人,再加上一个和尚和一个道士,总共大概130人。
当时官员数有统计。宋理宗宝祐时有2.4万多人。南宋汪元量有一句诗“满朝朱紫尽降臣”,说明大部分官员没有守节。尽管欧阳修提倡了死节、死义,但在大多数官员身上,并没发挥作用。
连文天祥的弟弟文璧也降了元。惠州城是他献给元朝的。元世祖说“是孝顺我底”。“底”字在宋代等于现在的形容词“的”。他送了元朝,是孝顺我的。文天祥给弟弟写诗,“弟兄一囚一乘马”——我是囚犯、你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我跟你是同一个父母养的,但是现在不同天,我是宋天,你是元天。
史实证明,无论是北宋末、南宋初,还是南宋末,大多数士大夫并没有响应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号召,做守节者或死节者。这就足以证明,尽管在一个强调名节的时代,儒家节义观的教育对宋儒所起的作用也不宜高估。
教育有作用,但是不能把教育作用夸大。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一方面受到儒家里一些好的教育,另一方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阶级社会不好的情况,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诱惑你。所以这个世界,某种意义上也是丰富多彩,不可能清一色。文天祥被俘到北方去,他说:“如果南朝用我做宰相,你打得过来吗?”南宋假如用了文天祥,真的打不过来,这是事实。但问题是,在官场筛选规律里,文天祥不到最后做不了宰相,能做宰相的是贾似道一批狐群狗党,文天祥也做不了。
课程简介
课程中,王曾瑜老师针对在中华古史研究中盛行一种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历史演进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教科文、军事等多方面的综合演进,被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动大众是历史演进的主干和主角。
古代的士大夫看来与近代的知识分子一词有相近之处,但绝不应把中国的士大夫都视为官宦。按照南宋陈亮之说,可以区分为“乡士大夫”和“卿士大夫”,后者才是官宦。古代士大夫中的大多数只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不应将所谓士大夫的群体视为社会精英,但士大夫中也确有个别的真正精英人物。
史料上的有善必录、隐恶扬善,使得史料中似乎士大夫精英们的比例比较大。其实,在阶级社会中,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多数是为富不仁,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如若仅仅摘取为富者仁、乐善好施的记录,那就是以偏概全。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为指导,方能对史学、对史料有科学的论析。
当代,有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但他们无非是以利己主义的心态、兼以实用主义的手段,去对待马克思主义。他们的最大特色,不是随风使舵,就是屈膝恶势。由此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恢复和强调古人倡导的名节观和气节观的重要性。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需要继承和发扬古人倡导的名节观和气节观,需要或应当强调有新时代内涵的名节观和气节观。
(视频拍摄于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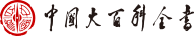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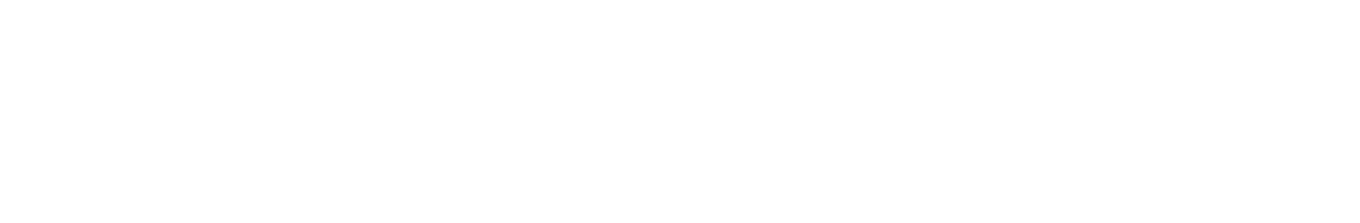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