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口学者K.戴维斯和J.K.布莱克(Judith Kincade Blake,1926~1993)首先提出。在戴维斯和布莱克所著的《社会结构和生育率:一种分析框架》里系统地论述了影响生育率的“中介变量”,并构建了理论框架。他们提出了影响生育率的3个大类:交配、怀孕和分娩;11个“中介变量”:男女开始同居(包括初婚)的年龄、永久性独身、不同居的时间、自愿禁欲、非自愿禁欲、性交频率、无生育能力、避孕、绝育、非自愿的胎儿死亡、人工流产。
在经济社会因素、中介变量系统和生育率之间建立了如下路径:
在以上路径关系里,古典和近代西方生育理论中社会经济因素与生育率的直接联系(图中虚线),被现代西方生育率理论中社会经济因素通过中介变量系统与生育率之间的间接联系(图中实线)所代替。
在中介变量理论模型中,11个中介变量与生育率的关系,有的为正相关,有的为负相关,因时间、地点的不同而不同。男女开始同居年龄和初婚年龄对生育率的影响方向通常是相同的,但是男女开始同居年龄和初婚年龄并不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一些发达国家里男女开始同居年龄呈下降趋势,青少年男女同居越来越普遍,由开始同居到正式结婚的间隔越来越长,这个期间的延长当然增大了怀孕的概率,但由于双方关系的不公开、不稳定,性交频率过高或者身体发育不健全等原因,同居者的生育率远低于初婚者的生育率。事实上,开始同居年龄的降低不一定会提高生育率,而且有可能因为上述原因以及习惯性流产、追求性享受等而使生育率降低,而初婚年龄的降低则一般会有助于生育率上升。同居是否一定导致结婚(主要指初婚),二者的关系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间可能很不相同。在性压抑、规戒较多的传统国家里,青少年同居者迫于社会压力而成婚者比重高于其他国家,从而造成生育率上升趋势。所以说,传统国家的一些社会压力在客观上是推动生育率上升的。
性交频率与生育率的关系也可能不是线性而是曲线式的,如果性交频率几近于0,生育率当然会非常低,但若频率过高,也可能因为精子质量不高而降低受孕率。而且性交频率过高者可能是最愿意避孕者,其生育率低下是由于避孕而不是纯粹生理原因造成的。不同居时间这个变量,也因为地区不同而对生育率有不同的影响,因此应注意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考察此变量和生育率的关系。
戴维斯等人主要是从人口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中介变量理论”的,由于中介生育变量的分类过于复杂,而且很难定量地研究它们与生育率的关系,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J.邦加茨(John Bongaarts,1945~ )对中介变量理论模型加以完善,从规范人口学的角度进行生育率研究,使得它在实证研究上更有可操作性,这种情况才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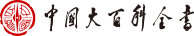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图 经济社会因素、中介变量系统和生育率之间的路径
图 经济社会因素、中介变量系统和生育率之间的路径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