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研究从收集文献向系统的田野工作的转换源于英国人类学家B.K.马林诺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屿的库拉圈研究。之后,人类学家普遍采用了这种不同于以前的书斋做派或短期旅行者做派的写作,而采用了长时段的参与观察的方式进入田野,提倡用内部视角进行实地调查。
田野工作主要收集的资料形式包括田野笔记,文字资料,影像、录音记录,图片,原文,图表及谱系表等。随着数码时代的迅猛发展,田野笔记的音像形式显得愈加日常化,它可以完整、立体地记录文化空间及其受访者的情感世界。田野笔记以记录、描述性素材为主。这些构成了撰写民族志的基本素材。
田野工作有以下3个特征或要求:①掌握当地语言。早期的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大都通过报道人[注]了解当地文化习俗,美国人类学家F.博厄斯认为语言承载文化,懂得当地语言是进入他者意识层面的最佳途径,因此人类学家一般被要求要掌握当地的语言。②长时段。根据研究课题的不同,一般田野工作不同于量化研究的方法,而是采用同在的方式,长时段参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在该过程中,进入田野的人类学者面临诸多挑战,如语言关、生理关、生活方式关、审美观、道德观及价值观等方面。③立场。与以研究者姿态、用宏大理论鸟瞰研究对象的立场不同,人类学者一般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相信实事求是的客观来自研究对象真实的生活世界。这一点涉及人类学的方法论,其中美国人类学家C.J.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1983)及M.D.萨林斯的《“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注](1995)颇具代表性。
田野工作的成果形式是民族志。它所涉及的不仅是方法本身,而更重要的是方法论。萨林斯认为所谓土著人和所谓文明人在动用符号理解自身社会和自然这一层面上并无本质区别;格尔茨认为脱离文化语境的研究者根本没有资格代表被研究对象;法国人类学家M.郭德烈[注]认为学者的研究欲望并不能等于被研究者的生活欲望;C.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研究者之所以看不到他者文化,是因为科学主义单向的理性思维方式所致。这些都构成了人类学者田野工作的信条和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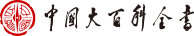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