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语言学经历了3次转向,深刻影响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理论和方法。3次转向都是关于意义的不同理解,探讨语言学转向实质是对20世纪人文社科理论发展的一个梳理。
第一次转向发生于20世纪前半叶的结构主义时代,学者将语言视为认识世界的“表征”或“再现”工具。语言的词汇和语法有内在结构,但其对语言使用者而言更多是无意识的存在。词汇的意义由字典定义而固定不变。此时研究重点在于寻找把单词组织成更大意义结构的规则。美国布拉格学派语言学家R.O.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1896~1982)的音韵学研究方法即从有意识的语言现象探讨无意识的基础结构。据此,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把人类学现象当作类似语言的系统来研究,在文化特殊性意涵中建构出人类知识的统一体。
第二次转向即阐释时代,意义由情境定义,是阐释的结果,研究重点在于寻找情境下阐释意义的技巧。在言语社区中,情境下的意义超越语法结构和字典。美国人类学家C.J.格尔茨认为,文化是一张意义之网,由同属某个社会文化群体的人合力编织而成。只有共同拥有这张意义之网的人,才了解其意义,也才能互相作用和理解。格尔茨提出“厚描”法,探讨人类社会经验的意向与意义,呈现意义之网,从而领悟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理解该意义在其社会生活世界中的位置。
第三次转向即“权力—话语”时代,意义不仅仅用来交流,更用来达成某些个体的目标。语言也是一种行动。研究重心在于探讨语言如何与权力结合,形成话语,塑造和改变人们的实践。法国哲学家M.福柯在《话语的秩序》(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中最早提出“话语即权力”,权力与话语共谋。话语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德国哲学家J.哈贝马斯指出语言是控制和社会权力的媒介,服务于有组织的权力关系的合法化,只要权力控制表现为合法的语言就是意识形态。这种话语—权力关系成为人类学实践理论的基础,即人类实践的效力在社会的权力网络中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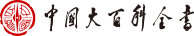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