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文化人类学先驱,但文化人类学仍是以美国为首的人类学主要传统之一。按美国早期人类学的划分,在人类学课程安排中与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并列,属于传统人类学的四大支柱之一。文化人类学从理论和方法角度可以认为是比较研究世界各地不同人群和文化、社会的学问;从学理角度看,它是把观念、意义系统[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不同文化的观念与价值[注]体系的学科。
 图1 B.K.马利诺夫斯基调查研究过的特洛布里安德岛上的妇女在准备晚餐
图1 B.K.马利诺夫斯基调查研究过的特洛布里安德岛上的妇女在准备晚餐
从学理角度看文化人类学,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化,如“广告”“时髦”“饮食”“戏剧”“诗歌”“小说”等,一般被理解为是一种大众化了的、外在的社会现象。文化的另一种表现是通过一定的积累或者特殊训练习得的,如“学历”“技能”“修养”等,且这种文化与教育体系、传统熏陶、经验积累及家庭教育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一种生存智慧和一整套成长经验的处世哲学,逐渐形成一种伴随人的生命历程而不断内在化的身体习性。
 图2 人类学家在危地马拉人中作实地调查
图2 人类学家在危地马拉人中作实地调查
英国人类学家E.E.埃文斯-普里查德主张,社会人类学首先是人文科学的一种,同时其方法学也是历史学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涵括在哲学范畴内。这是因为人类学研究不把社会、文化看成自然体系,而看成道德体系。费孝通也认为由于文化本身的特点,使人类学这门学科呈现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兼备的特征。在中国学术史背景下,有两点值得说明:①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区别。②文化人类学与中国的民族学的区别。
作为人类学的主要分支,社会人类学具有浓厚的英国和法国社会学传统,其中有英国社会人类学的中心人物。在学理上,社会人类学强调社会关系,进而讨论社会功能与社会结构及理论,侧重于把人与人、人与事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对象。事实上,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物质也可以组织人,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组织了人及其劳动,生产关系是一种组织模式,但它仍具有物质性。人在社会中,与其他文化的实体(物质)一样,其自身也是社会物质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经验个体。
文化人类学始终把指导人们行为习惯的思维方式作为分析对象(出发点并非“实体”本身),然后延伸到比较抽象的人和群体象征。包括共同幻想的共同体在内,文化人类学把任何一种人造物(如工具、衣食住行)的文化和社会本身都看成是一种人为的结果和现象。物质和现象本身并不具备文化人类学中文化的含义,它只是文化的产物,是一种客体[注]。文化人类学对智慧性造物及观念的物化十分执着,这是因为其主张观念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人类学概念中的观念与物质文化间虽有所区别,但又有着“形”与“用”,“体”与“魂”的关系,这也是当代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间产生广泛交流和合作的基础。法国人类学家C.列维-斯特劳斯认为:社会人类学致力研究作为表征系统的各类建制,文化人类学则致力研究各种实现社会生活的智慧,有时也包括被看作服务于各类建制的智能。在文化人类学家的眼里,“技术”也就是生存智能和智慧。随着全球化发展,文化对社会的影响不分国家和文化群体,当今的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基本上已合并为一体,其中法国人类学家P.布迪厄的研究堪称社会文化人类学[注]的代表。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划分除学科发展史上的意义外,基本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与价值。
在西方人类学发展历史中,夹在英国与法国两个文化大国间的德国和奥地利对人类学的发展发挥过特殊的作用。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发展出了“民族学[注]”和民俗学[注],而在美国则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德、奥的民族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紧密相连,擅长关注无文字社会,即部族社会;而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主要以文化为分析的基本单位,除针对历史性族人的关注外,还研究代表发达的、复杂社会的近现代文明社会的文化。跨历史、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其特色之一。如对摩尔根人等的早期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的影响在跨文化比较方面,表现出文化人类学研究较高的开放度。
中国的民族学也与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联系紧密,研究的基本目标或分析的基本单位是“民族”。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大规模民族识别,其结果呈现为苏联模式的四个统一标准(文化、语言、体质、信仰)下的民族分类学。这种分类学意义上的民族学强调与其他民族不同的衣食住行特色、语言习惯、思维和行为的独特性,淡化了人类在应当统一在“人”这一基本概念上的共同特性。这也是后来引起中国语境下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的主要原因。其中费孝通认为:“我们不要根据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分歧而影响到我们政治上的统一。”还有学者更强调了“心理的统一”。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出发点并非因民族研究其文化,而是从人们创造文化的视角出发去研究民族。该群体有时是同一民族,有时是族群,甚至是俱乐部、消费群体等其他群体,核心词是文化事实,也是分析和写作的基本单位。因苏联的影响,中国的民族学与国家意志、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相关联,走出了一条极具内敛、分类学色彩的民族学道路。它以民族为单位,集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文学为一体,学理上注重“是什么”的文化本质主义研究,这一点既不同于当今美国的民族学(即人类学)又不同于苏联的民族学。相比之下,文化人类学从文化出发,研究结果既是文化,也可能是意义、象征、价值、认同等。它既非社会人类学的社会关系实体,也非民族学的民族实体,承认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传承与传播两大轨迹所表现出的文化可塑性和可变性特点,同时还重视跨学科、跨地域、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能从摩尔根早期研究中获得启示,也是基于文化的可跨区域、跨文化的重要原因。“文化本质主义”“原生态”“无历史”的观点客观上削弱了文化的动态研究。
文化人类学承认文化是后天的,可习得的,所以它一开始就不是以文化本质为目的,它更注重人类思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事实上社会人类学所关注的“社会结构”“关系实体”“民族”在文化人类学看来都是某一文化的创造和后天的结果,是人间造物。随着全球化发展,世界各地的文化相互影响,经济利益以及消费圈也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赖局面。文化本质主义越来越受到挤压。出现了两种倾向:①文化保护主义。这一派反对全球化对传统、本土文化的侵蚀,反对文化变迁,最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②对全球化趋势采取积极态度,认为文化是可进化的。这一点表现在学术领域则出现了不同分支学科的趋同与合作。事实上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单一学科不能解决人类所面对的公共问题,如艾滋病、新型冠状病毒,它既是医学、公共卫生的问题,更是族群、社会制度和文化的问题。人们也更进一步认识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不考虑对话能力的单一学科发展及学术态度不宜人类整体、全面地健康发展。
 图1 B.K.马利诺夫斯基调查研究过的特洛布里安德岛上的妇女在准备晚餐
图1 B.K.马利诺夫斯基调查研究过的特洛布里安德岛上的妇女在准备晚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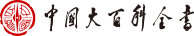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图2 人类学家在危地马拉人中作实地调查
图2 人类学家在危地马拉人中作实地调查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