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同化作为一种词义衍生现象例子如,唐孙樵《武皇遗剑录》卷五“蛊于民心,蚕于民生”中“蚕”的意思是“侵蚀”。“蚕”的本义是一种昆虫名,由此很难直接引申出“侵蚀”义。“蚕”的“侵蚀”义来自与它组合的“食”。“蚕食”是一个见于先秦文献的偏正结构,上古汉语中出现频率极高,《史记》中就有12例。在这个结构中,“食”的意思是侵蚀,“蚕”是名词作状语,“蚕食”义为“像蚕吃桑叶一样一点点侵蚀”。后来“蚕”受“食”的影响而有了侵蚀义,这就是组合同化的结果。
张博将“相因生义”“词义渗透”“同步引申”统称为“聚合同化”,她将“聚合同化”定义为“两个(或多个)词在某个义位上具有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词义运动的结果会导致它们在另外的义位上也形成同义(或类义、反义)关系。”
组合同化是有方向性的,制约同化的是组合体中两要素的语义地位。比如,偏正结构中被修饰性要素会同化修饰性要素,述宾结构中支配性要素会同化被支配性要素,述补结构中述语性要素会同化补语性要素。但并列结构中两要素的语义同化没有明显的方向,甚至还表现为双向同化。
组合同化的深层原因是上古汉语同义连用在双音节组合中的强势地位。并列式是上古汉语的强势造词法,而同义关系又是并列式中的强势语义聚合,由此可以推测,同义连用是上古汉语双音节组合中的强势组合。所以人们习惯于把组合在一起的两个词的语义关系理解为同义关系,从而用其中一个词的意义去类推另一个词的意义。
并列式和偏正式组合要素的高亲密度导致其间的语义差别易于被语言使用者忽略,因而这两种形式易于发生组合同化;而述宾式和述补式组合要素的低亲密度使语言使用者能较为明显地感觉到其间的语义差别,因此这两种形式很难发生语义同化。
参见词义沾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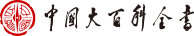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