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苏格兰东海岸的科卡尔迪,卒于爱丁堡。父亲是一名律师兼海关官吏,在斯密出生前就去世了,母亲玛格丽特·道格拉斯独自将斯密抚养长大。斯密的母亲是一位睿智的、虔诚的女士,为他选择受教育的方向。在科卡尔迪镇议会兴建的小学校里,斯密所受的教育奠定了良好的英语写作基础,培养了浓厚的古典文学兴趣;在学校之外,斯密从土地管理与改革、经商与政治等的争论中获益良多。1737年,斯密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当时的格拉斯哥是一个商业繁荣的城市。在那里,斯密遇到了“终生难忘的老师”F.哈奇森。哈奇森的道德哲学受到了自然法和沙夫茨伯里情感哲学的影响。在哈奇森的引导下,斯密开始接触D.休谟的《人性论》。1740年,斯密获得斯内尔奖学金,前往牛津巴里奥尔学院学习。当时的牛津大学充斥着教会的气息,要求严苛的宗教信仰却不重视教学,而且“反苏格兰人”。斯密在此感到失望。1746年,斯密离开牛津大学回到故乡科卡尔迪,未获学位。斯密的文人生涯始于H.霍姆即后来的凯姆斯勋爵的襄助。1748年,霍姆赞助他在爱丁堡开设修辞学和法学讲座。1748~1751年的讲座不仅让斯密在学界名声鹊起,获得超过100镑的年收入,还让他在1751年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授,此后又成为道德哲学教授。
自1752~1764年,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他讲授自然神学、伦理学、法理学和“策略论”或者经济学。自然神学的讲稿据说已经佚失,但斯密的学生J.米勒明确指出,在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讲稿中有一部分内容。伦理学和经济学的讲稿奠定了斯密后来的两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的基础,法理学讲稿在百年之后也在学生的笔记中再现。读者得以窥见斯密对实证法的性质的阐释,以及他对商业社会、政府形式等的描述。
1759年,斯密出版了他的第1部专著《道德情感论》。该书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C.汤申德读完此书后,决定以年薪300镑聘请斯密担任其继子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1764年,斯密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的职务,陪同年轻的公爵游历法国。1764~1766年2年时间,斯密游历过巴黎、图卢兹、法国南部,还到日内瓦待了2个月,其中在图卢兹待了1年半时间。在法国期间,斯密结识了J.le R.达朗贝尔、C.-A.爱尔维修、P.-H.D.霍尔巴赫等启蒙哲人,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重农学派的F.魁奈、H.–G.R.米拉波等人。1767年,巴克勒公爵在伦敦完婚,斯密随即回到科卡尔迪,并在那里创作其《国富论》,直到1773年春天,斯密认为自己差不多完成了书稿,打算带着《国富论》到伦敦交给出版商出版。寄寓伦敦的3年,斯密不断完善《国富论》。1776年3月9日,《国富论》终于出版。此书好评如潮,第1版很快售罄。1777年,斯密大约有10个月在伦敦度过,随后回到科卡尔迪。1778年1月,斯密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年薪500镑)和苏格兰盐税专员(年薪100镑)。自1778~1790年,斯密一直住在爱丁堡的潘缪尔宅邸中。1790年7月17日,斯密在这里终老,其墓碑上写着“亚当·斯密,《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的作者安眠于此”。斯密生前数次修改《道德情感论》和《国富论》,这一墓志铭足以代表他的一生。
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建构的理论,其实是与哈奇森、休谟、曼德维尔和卢梭等人的哲学体系进行的对话。在《道德情感论》出版之前,斯密已经发表了《致〈爱丁堡评论〉创刊人的一封信》,信中评论了卢梭和曼德维尔关于人性和初民生活状态的观点以及社会的形成等问题。在《道德情感论》中,斯密将同情或同理心设想为他讨论正义、良心、效用、习俗、美德等重要问题的基础。《道德情感论》分为7卷,第1卷是斯密的道德哲学体系的奠基石,论述人如何借助同情获得行为的合宜感。它将人的行为置于一般的社会交往之中,论述了人在不同场合下的情感反应以及如何才能做到合宜得体的反应。人天生具有的同情共感能力,使他们彼此能够感受对方的喜怒哀乐并做出即时的反应,以此为基础来判断行为的恰当性和合宜性。人们通过利用同情能力而得以形成一个群体的秩序和规则,在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超自然力量、王权、神权等)的影响下互相协作,进而组成社会,形成约束彼此言行的公序良俗。斯密的这种构想在他爱丁堡的法理学讲义中就初见端倪,在格拉斯哥的法学讲义中基本成形。人天生喜欢同情快乐而非悲伤,因而人自然而然会钦慕大人物而轻视地位低下的人,这是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力,也容易导致道德腐败;不过,这种天性也容易让底层人物积极进取企图改变自己的处境。只有在自然自由的社会体系中,底层人才有更顺畅的环境来“改善自己状况”。这是人们经济生活的动力。
在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人们在与他人相处时,总有一个“旁观者”来判断其行为是否合宜。“旁观者”并非斯密的独创,但被斯密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在论正义、良心以及责任感的那两卷中,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和内心的旁观者成为判断人们行为的法官。斯密在第1卷中指出,一种情感与其原因是否相称决定了它引起的行为是否合宜,其想要产生或实际产生的结果是有益还是有害,它引起的行为是值得报答还是该受惩罚。第2卷《论功过,或论赏罚的对象》明确了正义原则的3个层次:①不伤害他人的生命和人身安全。②不伤害其财产和所有权。③不伤害所谓的个人权利或因他人允诺而归之于他的权利。正是对受惠者、受害人和施惠者、加害人的双向同情使人们形成了正义的一般规则,进而形成了“公序”。“良俗”的养成则有赖于人们的良心。在斯密那里,良心是驻扎在人内心的那个“公正无偏的旁观者”,他像检察官一样审视这个人的言行,向法官一样裁决言行是否合宜。这个内心的旁观者,是每个人发挥想象力、依据同情心,将自己置身于更大的人群中反复换位思考的结果。良心不是上帝的神启,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同情共感的结果。
效用和习俗对18世纪人们的审美判断和道德认同有着很大的影响。休谟的效用论是斯密的争论对手。他在第4、第5两卷中论述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因效用和习俗影响审美判断和道德认同。第6卷是第6版《道德情感论》新增的内容,讨论德性的品质。斯密在这里论证了德性、自制与合宜感的关系,尤其是谨慎、骄傲、虚荣之类的品质,后者似乎暗示了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最后1卷是斯密对历史上各种道德哲学体系的评论,表明自己将另文撰述法理学的相关问题。
斯密自己认为《国富论》兑现了《道德情感论》许下的部分承诺。这表明他并没有把这两部著作当作完全割裂的作品,也意味着并不存在后来所谓的“斯密问题”。《国富论》的本意是“探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但它不是一部只探索“财富”的著作。斯密在书中的经济分析理论,例如劳动分工、生产与分配、价格理论等,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炮轰”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此之前,英国的休谟、法国的米拉波等人曾撰文抨击重商主义。斯密要做的是彻底颠覆重商主义的根基,倡导“自由贸易”的政策,希望建立“完美的自由体系”。这种颠覆不仅针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还从人性的本质出发解释财富的真正性质和增长的原因。因此,《国富论》可以说在经济生活层面构成斯密的“人的科学”体系。
该书共有5编。第1编讨论劳动生产力提高和改进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状况的人们中间被自然而然分配的次序。第2编讨论资本的性质,它的逐渐积累的方式,以及依它的不同运用方式所推动的劳动的不同数量。第3编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叙述财富自然增长的历史和欧洲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这一编中,斯密从不动产到动产的财富转变宣告商业社会的到来,并引入了经济增长中的法律和历史要素。欧洲的政策偏向城市手工业和制造业,并最终导致扭曲了斯密所说的“自然进程”。如此引申出来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对经济政策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的公共管理都产生了影响。《国富论》第4、第5编便是对这些理论及其影响的论述。前4编的目的在于说明是什么构成了广大民众的收入,第5编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在《国富论》中,斯密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立法者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有二:“其一,为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其二,给国家或共和国的公共服务提供充分的收入。它旨在富国裕民。”因此,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关心的不单是国家在经济事务上面临的问题,还有政治、法律和历史层面上的问题。这也使得《国富论》的谋篇布局显得有些杂乱。尽管在刚出版时受到好评,但在斯密去世时,英格兰、苏格兰社会的评论却认为,与休谟等人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相比,“斯密博士的体系与他们并没有本质区别”。后来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J.A.熊彼特对这部著作做出了更低的评价。这种评价轻视了斯密留给后人的思想遗产。
斯密一生为人谨慎,即便在信件中也很少公开自己的政治立场。1793年,D.斯图尔特在爱丁堡皇家学会宣读的《斯密传》,更像是作为斯密的辩护人,为他洗脱欧洲政治旋涡给他带来的各种嫌疑。但斯图尔特塑造的形象并非真正的斯密。1790年,斯密的遗嘱执行人在他的要求下烧毁了他的绝大部分手稿,剩下的唯有收录在《哲学论文集》中的残篇。如今,斯密给学生上课的法学讲义以及斯密的藏书都已被整理出来。法学讲义中的推测史、四阶段论以及社会理论显露出来。斯密的思想遗产逐渐展现给这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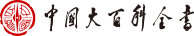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