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出《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李梦阳传》:“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此书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表述相近。这一概括旗帜鲜明、简明扼要,后常被人引用,并被用于通论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思潮。但它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表述是文章师法先秦、西汉,五言古诗师法汉、魏,歌行、近体师法李白、杜甫和初、盛唐诸家。
先秦两汉和盛唐是中国古代散文和诗歌的黄金时代,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在明弘治朝登进士第,欲弘扬古学,于是选择古代诗文的最佳典范,本意是要从中获得古人个性与规范完美结合的真诗精神,从而革新明代流行已久而疲软不振的台阁体与性理派诗文风格。但他们很快遭遇刘瑾乱政,在正德年间的混乱政局中,无法在更广泛的政治文化领域有所作为,只好以诗文(尤其是诗歌)自负。李梦阳、何景明在如何学习古人的理念上有分歧,导致了文学史上著名的李何论争。对于这场纷争,《明史》的判定是“李主模拟,何主创造”,但其与事实有较大出入。李梦阳强调学习古人要从体制声调等形式规范入手,何景明则主张师法古人的“神情”。何景明之说虽可避免过求形似之失,却也没有摆脱学习和模仿的道路,因而不可称为“创造”。
李梦阳、何景明本希望以复古为契机,革新文体与文风,但未能实现这一初衷,因此在文学史上被贴上了复古主义的标签。《明史》用“必”字强调他们对古代文学遗产过分的拘守。
嘉靖(1522~1566)中期,在严嵩专权误国的政治生态下,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再次揭起复古的大旗,他们的文学活动与险恶政治对抗的意图更明确,采取的师古策略也更极端。李攀龙对先秦散文、古乐府和汉魏古诗的模仿甚至亦步亦趋,文学复古走入了更狭窄的道路。相比之下,他们对初、盛唐近体诗的学习相对圆活,更能体现何景明“领会神情”这一理念的传承。王世贞提出“师匠宜高,捃拾宜博”的看法,已经初步突破了对第一义的拘守,晚年又提出“用宋”“有真我而后有真诗”等主张,进一步拓宽了复古派的诗歌疆域。他还倡导剂、辞达等主张,丰富文章的审美内涵,强化其可读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他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也高于后七子其他成员。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致代表了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从文学角度看,这种主张基本无可取之处。前后七子也有较好的诗文作品,但都是真情所至,与是否“必秦汉”“必盛唐”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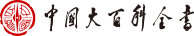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