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罗马。曾在罗马大学接受教育。受20世纪60年代法国哲学家J.德里达和M.福柯的影响,但受I.康德、G.W.F.黑格尔、M.海德格尔和W.本雅明的影响更大。曾在1966年和1968年参加过海德格尔所开设的研究赫拉克利特和黑格尔的研讨班,此外,他还受到亚里士多德和C.施米特诸多思想的影响。曾在意大利、瑞士和法国的多所高校任职。他在本质上属于批判和解构型理论家,习惯于采用一种前卫的研究视角。最初主要关注于语言研究,同时也关注美学产生的形式和功能,以及艺术家的角色等。代表著作有《神圣人》《例外状态》《奥斯维辛的剩余》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审视当约束人类行为的所有规则似乎都在消失的时候,所会发生的事情,即暴力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他常常会关注到似乎被许多理论家忽视的人类生活的诸多重大问题,其文风和写作方式常被人们认为艰涩难懂。
在阿甘本早期著作中,他论述了语言的意义及其作为一种理解存在的方式而在形而上学史中所处的位置。依照其观点,形而上学的历史将语言理解为获取或接近超验存在的手段。这种超验性的存在是超越于我们的世俗存在和知识之上的,是人能够认识的深刻真理。在其著作《初创期与历史》中,阿甘本认为超验事物不是在语言之外,而是在语言之中。在其著作《语言与死亡》中,他对此观点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发,对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作了进一步的引申。阿甘本认为,死亡在政治学、法律和社会控制的世界中演绎出来。“神圣人”开启了阿甘本对于作为法律、人性、政治学及主体的主权的长期探索。他聚焦于“赤裸生命”观点上。“赤裸生命”也就是基本上剥除了所有人类特征的人类,而这种剥夺的程度在纳粹集中营中是最大的。在现代性的“生命政治学”中,赤裸生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依照阿甘本的看法,它必须通过西方文化溯源到古希腊罗马法律中,西方现代性使得生命成为受控制的主体。因此,主权必须建立在生命政治学之上,集中营几乎是一种对人类社会本质的回归。“赤裸生命”是阿甘本对语言之反思的延伸,它是一种空壳的人性,既不很人性也不很动物性,甚至当它出现的时候,也是作为一种过渡状态,它被推入背景之中而成为建立在法律之上的社会的一部分。阿甘本认为,政治生命建立在惩罚的基础之上,尤其是被杀害的可能性上。阿甘本探讨了例外状态——法律悬置的状态。这也就是法律被建立的时刻,它本身既不是合法的也不是非法的,而是暴力的。自然的暴力被压制起来进行重新组建,成为保障所有其他的例外状态。依照阿甘本的观点,这不仅仅是权威的神圣缘起,而且也是一种不会消散的潜力,是现存制度永远不在场的部分。而在天平的另一边则是“神圣人”。在阿甘本看来,所有的现代生活都朝向“生命政治”和化约为“赤裸生命”,即人类越老越变得完全屈从于规则和秩序,屈从于例外性,越来越少地作为主体而存在。这种“纯粹”的法律状态既不必然是好的或坏的,它被强化的地方是集中营,其中例外成为了规则,所有的人都成为了“赤裸生命”。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中,阿甘本深入探讨了这个主题。其目的是拒绝其他理论著作中存在的那种“不可言说”的神秘主义方式,重新思考纳粹集中营。他并不试图揭示出一种关于人类境况的永恒真理,而是一种历史性的真理,发生在带出了某种原始而社会性东西的特定时间、政治和语境中的真理。在对施密特主权理论的阅读中,阿甘本回到了对“例外状态”的探究,这集中体现在其《例外状态》一书中。
在对政治的理论回归中,阿甘本是一个重要的动力。在对生命政治制度及在个体和文化层面对存在之现象学解构上,他的理论工程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将福柯等思想家研究的生命政治学继续向前推进和深化。他的阅读范围和伦理动机使得他成为任何自我反思的政治哲学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阿甘本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思想家,他对其他哲学家著作的解读常被指责有断章取义之嫌。批评者认为其著述阴冷、悲观,对于思考政治行为几乎没有用处,或认为其内容深奥、空洞及荒谬。颂扬者则认为他是在思考克服当前不断加剧的虚无主义之诸多条件,以及反思后资本主义情景下社会生活的堕落,是对当代全球政治之具有洞察力和警醒力的批判性诊断,是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之可能性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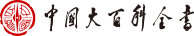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8139号
